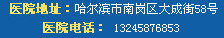引言
毋庸置疑,“人类”这个于宇宙宏观庞大的角度看来,不过是停留于地球上的一种过客,于整个宇宙史而言可谓是不值一提;然而,于自身看来,我们却是有别于同一物种中的其他动物的。是矣,我们将自己定义为“高级动物”。
我们的各种集体不限制成员人数,只要大家接受、我们自身愿意融入,这个集体便会愈来愈大。这也就是为何说“人除了是高级动物外,也是社会性动物”。
在社会交往中,我们通过语言、动作以及表情将我们自身的精神意志对外输出,与他人的精神意志发生相互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因精神意志不同产生的冲突。
是矣,我们在调节这难以避免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矛盾以及人与社会相融合的矛盾过程中,产生了“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文明”。
作为我国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及“香草美人”之“虽九死其犹未悔”而流传史册的汉朝,更是将各个集体、各个国家文明之间的“不打不相识”尽情演绎。本文将对汉代器物却可体现西方文明身影做出详细解释。
一、浅尝辄止还是拿来主义
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自然会使其所处的环境、所交往的人以及每天的言谈举止注定不同。是矣,其对同一事物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尽相同。
不然,何以解释历朝历代均会设置“策士”、“谋士”一类的官职,专以用来分析各种形式进而出谋划策。这也就导致在面对同一种“外来文明”时,大家注定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态度,而这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三类:
①极度坚持本土文明为“优势文明”,对于“外来者”全盘否定。
②坚持自我文明的同时,适当接受“外来文明”。
③总是认为“物以稀为贵”,认为自己所拥有了的便不是“优秀文明”,便不再具有传承价值。而选择抛弃本土文明,全盘接受“外来文明”。
至此,不免疑问道:既然标题中讲‘汉朝器物中出现了西方文明的身影’,那其对西方文明究竟是持有怎样的态度呢?是第二种的理性吸收还是第三种的“拿来主义”?
若是第二种的理性吸收,又吸收了哪些呢?吸收后又是如何于载体中呈现的呢;若是第三种的“拿来主义”,为何于史册之中却毋庸置疑,“人类”这个于宇宙宏观庞大的角度看来,不过是停留于地球上的一种过客,于整个宇宙史而言可谓是不值一提;然而,于自身看来,我们却是有别于同一物种中的其他动物的。是矣,我们将自己定义为“高级动物”。
我们的各种集体不限制成员人数,只要大家接受、我们自身愿意融入,这个集体便会愈来愈大。这也就是为何说“人除了是高级动物外,也是社会性动物”。
在社会交往中,我们通过语言、动作以及表情将我们自身的精神意志对外输出,与他人的精神意志发生相互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因精神意志不同产生的冲突。
是矣,我们在调节这难以避免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矛盾以及人与社会相融合的矛盾过程中,产生了“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文明”。
作为我国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及“香草美人”闻名而流传史册的汉朝,更是将各个集体、各个国家文明之间的“不打不相识”尽情演绎。本文将对汉代器物却可体现西方文明身影做出详细解释。
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自然会使其所处的环境、所交往的人以及每天的言谈举止注定不同。是矣,其对同一事物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尽相同。
不然,何以解释历朝历代均会设置“策士”、“谋士”一类的官职,专以用来分析各种形式进而出谋划策。这也就导致在面对同一种“外来文明”时,大家注定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态度,而这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三类:
④极度坚持本土文明为“优势文明”,对于“外来者”全盘否定。
⑤坚持自我文明的同时,适当接受“外来文明”。
⑥总是认为“物以稀为贵”,认为自己所拥有了的便不是“优秀文明”,便不再具有传承价值。而选择抛弃本土文明,全盘接受“外来文明”。
至此,不免疑问道:既然标题中讲‘汉朝器物中出现了西方文明的身影’,那其对西方文明究竟是持有怎样的态度呢?是第二种的理性吸收还是第三种的“拿来主义”?
若是第二种的理性吸收,又吸收了哪些呢?吸收后又是如何于物质文明中体现的呢?
无从考察?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二、精神意志深度理解物质文明加以体现
如引言中所提:“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我们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而“社会生产力”,顾名思义:通过一定的劳动生产出满足我们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产物亦或是满足我们精神建设的产物,进而循环往复。
恰巧,这套循环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文明”与“精神”总是形影不离、休戚相关。至此,难免质疑:那跨越至今千年的汉朝已然是诗歌发展的高峰,其本土文明于己而言,自然可谓是一览众山小。那么,其对于“外来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是否也遵循上述循环呢?遵循循环是否等同于全盘接受呢?
或许基于以下所提,我们可以找寻到部分答案的踪影:
薄雾缭绕,云山相接之美景,自然是飘飘然于其间者如住仙境。据史料记载,我国汉朝时期,不仅已经有香炉的出现,而且这缭绕于仙山之上的“紫烟”正是由“香炉”散出。
切莫急于质疑:仙山之上的紫烟怎么可能于短时间内由香炉发出?或许汉朝墓穴中的“博山炉”可以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于此,便以史料记载最为详细真实的出土于西汉中山王——刘胜之墓的“博山炉”为例。
由于年代久远,该香炉出土时难免带有历史的痕迹。然而,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见,香炉上部的所置下的仙山正是“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中的“蓬莱山”。
我国幅员辽阔、壮丽山河最富盛名。拥有不计其数、独具特色的巍峨之山,为何单就置下“蓬莱山”?李商隐怕你我疑问于此,下句便已经将答案告知:蓬莱山无路可通。我们暂且不论诗人由于当时所处境况而借此发出的引申义。仅取表面义,已经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
蓬莱山又名“九仙山”,历史留下了太多类似“百丈自天垂瀑布,五云佳气接蓬莱”有关“蓬莱山”的诗词了。其中“会待功成插翅飞,蓬莱顶上寻仙客。”便直接将“蓬莱山”与“仙人”相连接。久而久之,我们为之所熏陶,每每提及“蓬莱”便于潜意识中直接将其与“仙人”“仙山”以及“仙境”相连。
自然,“诗词”与诗人本身而言,又何尝不是其精神文明体现的载体?于受其熏陶的读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其“诗词”对我们精神文明的建树呢?何尝不是“物质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精神得以延续保障的前提”的再一次释义呢?
只是,将“蓬莱山”视作“仙山”的这种意志最初源自何处?又是借谁之手传出的呢?除了“博山炉”之外,是否还传出了其他文明?
西方学者罗森在其论文中这样讲道:中国西汉出土的“博山炉”是基于西亚文物灵感而创作的。为加强该论点,罗森将西方石雕上的香炉与自土耳其出土的墓中香炉相比对。
不论是于时间方面亦或是文物艺术形式都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其论点。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朝时期已经接受“外来文明”,且是借助工匠之手将其推广。如上文所言“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其推广之途径隶属工匠,也是意料之中。至于接受至何种程度,接下来的这个有趣且已为数代民众所接受的形象,便可解答一二。
众所周知,“瑶池西母”这一形象出自《穆天子传》,而“瑶池西母”盼周穆王可“复来”这一虚构神话不仅讽刺了周穆王一属者异想天开意图升仙长生,且其侧面体现了“瑶池西母”这一人物已与“仙境”“长生”密不可分。
而这密不可分的关系亦是要从来自公元前年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库巴巴这一女神身上寻找答案。这件趣事也就此展开:既然知道西王母这一形象源自“西方文明”,那为何中方的“西王母”与西方的“巴巴女神”却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两者的“头饰”?
在解释这一问题之前,要补充一条史实以助理解——我国汉朝最初并没有“椅子”。但此时西方国家不仅已经开始使用“椅子”,而且在雕刻雕像时也会适当将“椅子”这一元素融入。
这就导致我国汉朝工匠在创作“西王母”这一形象时误将“巴巴女神”所坐的椅子与所颈部连接的部分理解成为了“巴巴女神”头戴的饰品。故,至今为止,你我印象中的“西王母”均是头戴饰品的形象。虽然是误判,但这“误判”间接导致了“误解”,进而由工匠之手创造出了独具我国特色的“西王母”形象。
由此观之,我国汉朝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于自身理解之后,加以融入本土文明的。并非“全盘接受”亦或是“拒之千里之外”。如此,虽然上文中所持有的疑问解决了,但当时汉朝工匠为何就可以保证在融入自己对“西方文明”适当理解之上的手工制品亦或是器物就可以为当时君主、百姓所喜爱呢?
毋庸置疑,于工匠而言,若是自己所创作的产品没有市场久而久之自然濒临破产,难以维系生存。
正所谓“有需求才会有产品,进而才会有市场”此前,悅克鲁对汉代贵族王室、诸侯等墓中所发现外侧绘有“水滴”状花纹的圆形银盒做出过一系列考察研究。发现汉朝贵族大多均是偏爱“圆形银盒”这一舶来品的,但是于墓中所发现的圆形银盒并非真正的舶来品,而是由汉朝工匠自己铸造而成,原因为何?
铸造手艺不同,其给人的视觉感受自然也会不同。源自罗马的圆形银盒所采用的铸造手艺是“锤牒工艺”,其产品壁层较薄;而出土于我国汉朝时期的圆形银盒很明显具有“壁层较厚”的特点。据史料记载,这种“壁层较厚”的艺术美正是我国当时汉朝上流贵族所偏爱的艺术形式。
这就不难推断出:我国汉朝工匠为迎合贵族艺术审美需求,在适当理解具有“西方文明”一直的舶来品艺术形式后,融入了当时贵族的审美观念。以求“浇灌法”所铸造出来的壁层较厚的圆形银盒可以得到贵族的青睐,继而维系产品市场。
三、包容理解外来文明坚持创新本土文明
上文所示,已于不觉间阐述了汉朝社会发展的一个事实:其文明发展也同样遵循第二部分开头所阐述的一套循环程序。若说这套循环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相发展的必然,那汉朝工匠将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文明”融入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念,想来定是人为主动的因素了。
不难发现,本文所提及的积聚汉朝文明的器物选取的均是源自汉朝墓穴中的器物,而与之相比对却是西方文明中的种种壁画中的器物亦或是种种神话中寿命永昌的神人。为何将这两者相提并论?是否有亵渎神灵之嫌?
基于此,可以给出明确回答:并不具有亵渎之意,反而是一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尊重。回望历史,绝大多数的迁客骚人无不在其诗词中阐述一番自己的“生死观”“宇宙观”。
譬如东坡先生便曾将人类之于宇宙之渺小的事实阐述得一阵见血。试问:古往今来,哪一个朝代的君主、帝后以及贵族不渴望王朝永存,自己永为帝君?
就连《楚辞》之主都曾言:即使自己立刻死去,都不会与其同流合污。灵均一生“香草美人”的形象已不容置疑,于此却以“立刻死亡”为赌注。由此观之:古人之生死观已然是刻于心骨。
是矣,除了古人墓中之“文物”还有什么可以深刻阐释其“生死观”的文物吗?不仅汉朝在文物中适当融合了西方文明,而且直至汉朝后期其墓室建筑材料也适当地采用了西方的墓室建筑材料——石头。此外,也效仿西方之画像石、画像砖以及石刻镇墓兽。
这一现象无疑将我们置于本小节开始的疑问做出了明确回答:在汉朝,“西方”与“仙境”是紧密相连的,是集聚“仙寿永昌”之意的。不然何以所谓“驾鹤西去”?是矣,将我国汉朝于墓室中出土的文物与西方神人相提并论并不具有亵渎神灵之意。反而,是一种基于西方文明深度理解之后的,所创新的本土文明。
结语:
所谓“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但“新”并不是要摒弃所有本土文明,将外来文明全盘接受。我们已经习惯本土文明所铸造的环境,我们的意识与我们本土文明的意志是具有一致性的。
于动态历史发展的航程中若是限于本土文明的舒适圈,必然要为史所弃;若是全盘接受外来,久而久之,势必也会如同邯郸学步一般。
这就要求我们于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站在坚持本土文明的立场之上,以开放包容之心态适当接受外来文明。既不囿于定论,也不迷失自我。
参考文献:
《中华古建筑》
《乐山、彭山和内江东汉崖墓建筑初探》
《汉书》
《楚辞》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7288.html